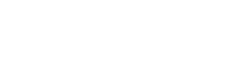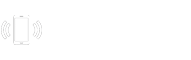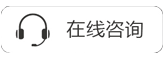那只宋徽宗畫上的鶴,終于落在了他死時(shí)的衣服上
作者:147小編 更新時(shí)間:2024-11-17 點(diǎn)擊數(shù):
“曼衍魚龍戲,簇嬌春羅綺,喧天絲管。霽色榮光,望中似睹,蓬萊清淺。”
“東風(fēng)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dòng),玉壺光轉(zhuǎn),一夜魚龍舞。”
宋朝,像一個(gè)夢,被歌詠與追憶制造的繁華綺麗,簡直不像這世間應(yīng)有的存在。讓人忍不住想抓住這夢的殘片,這或許也是當(dāng)《瑞鶴圖》,這一被歸于歷史上最富才情的北宋帝王趙佶名下的畫作每次開展,都會(huì)引得眾人趨之若鶩。排了三十分鐘的長隊(duì),只為看它三十秒——盡管那只是短短的一瞬,卻是入夢的一瞬。
追憶宋代生活的兩部名著《東京夢華錄》與《夢粱錄》都有一個(gè)夢字。因?yàn)樵趬糁校倌戟q如一瞬,在夢中,一瞬恍若百年。無盡的繁華,都可以濃縮在一瞬間綻放,三百年的歷史,也可以在一個(gè)個(gè)瞬間中呈現(xiàn)。
這瞬間,是宋太祖面對(duì)眾將端起酒杯的瞬間,是宋真宗簽下澶淵之盟的瞬間,是熙寧變法下田夫的一聲長嘆,是靖康之變中被擄走的宋欽宗那一聲“百姓救我!”的瞬間。在這瞬間中,可以聽到孟珙郁郁而終前,那一聲“今志不克伸矣”的悲鳴,可以聽到樊城下回回炮發(fā)出的轟鳴,也可以聽到被宋人扣押在真州館驛十六年的元朝名臣郝經(jīng)那意味深長的沉默。
在時(shí)間的河床上,瞬間猶如朵朵浪花,有的在磐石上砸得粉碎,有的則沖決崖壁,有的則緩緩潛入暗流之中。無論是激烈的、悲壯的、荒誕的、無奈的、哀傷的、庸常的,無量無數(shù)的瞬間,都匯入了歷史的長河中。盡管唯有那真正把握歷史的瞬間,才會(huì)在歷史長河中成為永恒,然而逝者如斯,未嘗往也,所謂的永恒,也不過是眾多瞬間簇?fù)淼囊欢淅嘶ǎK將成為過往。
但唯有經(jīng)歷過那個(gè)瞬間的人,才有資格如是說: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本文出自書評(píng)周刊10月25日專題《大宋的十三個(gè)瞬間》B04-05版。
撰文|李夏恩
仙鶴
清曉觚棱拂彩霓,仙禽告瑞忽來儀。飄飄元是三山侶,兩兩還呈千歲姿。
似擬碧鸞棲寶閣,豈同赤雁集天池。徘徊嘹唳當(dāng)?shù)りI,故使憧憧庶俗知。
——趙佶《瑞鶴圖詩》

《瑞鶴圖》畫心部分。
鶴,飛來的時(shí)候,仿佛將暮色一并帶入了這上演著如夢繁華的都城。
如果那個(gè)名叫閻德源的十八歲少年,在此刻抬起頭,他會(huì)看到一幅如畫般奇麗的景象。夕陽被晚霞熱烈地熔化,宇宙深邃而澄澈的青色才顯現(xiàn)出來,帶著吞噬萬物的帝王般的威嚴(yán)降臨在這片大地上,卻又被這倏然飛來的仙鶴所打斷,它們潔白的羽毛雖然漸次被暮色所染,但在深青色的天穹上,依然猶如不甘退卻的白晝,刻意安排在夜色中徘徊翱翔。下方升起的杏黃云霧,恰到好處地遮住了這群仙鶴的來路,讓這些本有仙禽之稱的飛鳥,真如天仙降臨般神妙莫測。
或許,直到它們發(fā)出那被贊為聲達(dá)九天的鶴唳時(shí),下方的喧嚷的人群才注意到它們不知何時(shí)已經(jīng)盤旋在了自己的頭頂,翱翔在眼前這座寓意不言自明的恢弘建筑之上。
宣德門,這座巨大的城門巍然屹立在東京汴梁的中心,標(biāo)記著帝王與臣民之間判若云泥的界限。作為一名生于茲、長于茲的東京人,閻德源自然對(duì)此萬分熟悉。在他還是孩童時(shí),這座城門多少還浸染著一些市井紅塵的氣息,小商小販會(huì)在城門兩旁的御廊里高聲叫賣,平民百姓也可以在門前的御道上自由地行走。但這一切都在不久前被粗暴地打斷了——御廊安立了黑漆杈子,路心又安立了朱漆杈子兩行,中間的御道從此不再允許人馬行往,平民百姓只能在廊下朱漆杈子之外,遠(yuǎn)遠(yuǎn)地仰望這座帝王禁宮的大門。
但上元節(jié)期間,這座禁絕行人的禁宮城門卻會(huì)像它的主人一樣,臨時(shí)展現(xiàn)出它仁慈的一面,“縱萬姓游賞”。城門前會(huì)豎起巨大的鰲山燈,草扎的兩條巨龍盤繞在沖天的鰲柱之上,大小燈盞遍懸龍身,猶如發(fā)光的鱗片,在夜空下熠熠生輝。鰲山中則高懸御榜,金書大字“政和與民同樂萬壽彩山”,宣示著將這如此輝煌盛景恩賜給京城百姓的人究竟是誰。
然而,這自詡與民同樂的天下恩主——趙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上元這天卻不會(huì)出現(xiàn)在臣民面前。盡管這天才是歡慶的高潮,但他要前往皇家道觀上清宮為自己,也為自己所主宰的大宋天下祝禱祈福。直到上元之次日,他才會(huì)在進(jìn)過早膳后,登上宣德門的城樓,端坐在御座上,俯瞰城門下熙熙攘攘企圖瞻仰帝王御容的萬千臣民。
那是一場君臣合作的恩威并施的盛大表演,“樓上有金鳳飛下諸幕次,宣賜不輟。諸幕次中,家妓競奏新聲,與山棚露臺(tái)上下,樂聲鼎沸。西條樓下,開封尹彈壓,幕次,羅列罪人滿前,時(shí)復(fù)決遣,以警愚民。樓上時(shí)傳口敕,特令放罪。”暮色時(shí)分,這場表演由一場“華燈寶炬,月色花光,霏霧融融,動(dòng)燭遠(yuǎn)近”的華燈盛會(huì)邁向尾聲,直到三鼓時(shí)分,這場華麗而盛大的恩威表演才隨著樓外的擊鞭的聲響宣告結(jié)束。宣德門前鰲山上下的數(shù)十萬盞燈燭,“一時(shí)滅矣”。
年復(fù)一年,歲歲如此,在這京城中長大的閻德源以及萬千汴梁人,對(duì)這套君臣同樂的表演儀式已經(jīng)相當(dāng)熟悉。但在政和二年正月十六日這天,這一常規(guī)套路卻被打破了,而打破這一切的,正是從宣德門城樓上升起的杏黃煙云中,倏然出現(xiàn),飛鳴于碧青暮色之中的一群仙鶴。
奇景

《瑞鶴圖》題詞部分。
“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門,眾皆仰而視之。倏有群鶴飛鳴于空中,仍有二鶴對(duì)止于鴟尾之端,頗甚閑適。余皆翱翔,如應(yīng)奏節(jié)。往來都民無不稽首瞻望,嘆異久之,經(jīng)時(shí)不散,迤邐歸飛西北隅散。”
閻德源當(dāng)然沒有見過這段題詞,也不會(huì)見到配在這段題詞右邊描繪這一場景的畫作——題詞和畫作都只屬于它的創(chuàng)造者宋徽宗本人所有。但如果他和其他汴京百姓一樣,站在宣德樓前,畫中呈現(xiàn)的仙鶴飛鳴的奇景,他應(yīng)該可以看清一二。只是他眼中所見,未必盡如畫中所繪一般。
盡管畫中輝煌的殿宇、碧青的天穹,與飛翔的仙鶴,似乎都栩栩如真,但如果看得仔細(xì),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其中錯(cuò)漏頗多。
宋徽宗在題詞中特別提到的“二鶴對(duì)止于鴟尾之端,頗甚閑適”就是一個(gè)典型的例證。因?yàn)辁Q腳趾的生物構(gòu)造并不善于抓物,它甚至連一般飛禽棲息的樹枝都無法站穩(wěn),因此,無論如何,它都無法穩(wěn)穩(wěn)地抓牢并站在滑溜溜的鴟吻頂端。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鴟吻上本就不應(yīng)出現(xiàn)任何鳥雀。根據(jù)北宋建筑規(guī)制,高等級(jí)的宮殿城樓的鴟吻,都被刻意安裝了防止飛鳥在上面棲息的鐵質(zhì)構(gòu)件“拒鵲”。就這場鶴唳城樓的奇景發(fā)生的九年前,朝廷剛剛頒布了官方建設(shè)施工規(guī)范書《營造法式》,上面明確寫到“凡用鴟尾,若高三尺以上者,于鴟尾上用鐵腳子及鐵束子安搶鐵。其搶鐵之上,施五叉拒鵲子”。以宣德門這般國門規(guī)制的城門,鴟吻上自然會(huì)安裝驅(qū)逐落腳鳥雀的拒鵲。仔細(xì)觀察畫面,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在鴟吻金色的搶鐵之上,有一排整齊的墨線,那就應(yīng)該是拒鵲。只是在帝王御題的圖畫中,這尖利生冷的五叉拒鵲,就像平日里安置在宣德樓前御路上的朱漆杈子一樣,只是用來驅(qū)趕平民百姓一般的凡俗鳥雀,但遇到鳥中高貴的仙鶴,卻會(huì)收斂起它尖利的鋒芒,成了軟塌塌的幾根墨線而已。

站在鴟吻上的仙鶴。
當(dāng)然,除了這處細(xì)節(jié)中違反仙鶴生物構(gòu)造的錯(cuò)誤外,鳥類學(xué)家陳水華在《形理兩全》中指出,畫作中還有另外兩處錯(cuò)誤,“一是丹頂鶴次級(jí)和三級(jí)飛羽是黑色的,只有初級(jí)飛羽是白色,但徽宗卻把次級(jí)飛羽也畫成了白色;還有就是,丹頂鶴飛行時(shí)脖子是直的,圖中卻把鶴的脖子畫彎了”。雖然挑出這種毫末錯(cuò)誤多少有吹毛求疵之嫌,但將其施于宋徽宗身上卻相當(dāng)恰切,畢竟,宋徽宗本人就是一位吹毛求疵的大師。

《瑞鶴圖》中彎頸飛翔的仙鶴。
根據(jù)宋人筆記《畫繼》中的記載,一次他令畫院眾人描繪孔雀升高站在藤墩上的圖畫,所有人的畫作無論如何“各極其思,華彩燦然”,得到的卻只是徽宗一句“未也”的評(píng)價(jià)。愕然莫測的畫師們?cè)诙嗳蘸竺鎸?duì)皇帝依然不知自己犯了何等錯(cuò)誤,直到此時(shí),徽宗才告訴他們:“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而他們畫的全是先舉右腳。于是畫師們紛紛為皇帝的明察秋毫而“駭服”。
連孔雀升高先舉哪只腳爪都觀察入微的皇帝,居然會(huì)在描繪他最喜愛的祥瑞靈禽仙鶴時(shí)犯下這樣的錯(cuò)誤,委實(shí)讓人疑竇油然而生。但從另一個(gè)角度考慮,這些疑問或許都可以得到解釋,那便是徽宗皇帝本人或許根本沒有見到這一奇景。
當(dāng)這一仙鶴翱翔在宣德門上的奇景發(fā)生時(shí),徽宗皇帝并不在下方延頸仰望的萬千百姓中,而是面對(duì)百姓,端坐在城樓的御座之上——他和作為這一奇景的仙鶴一樣,都是供百姓仰望的對(duì)象——從某種意義上說,那飛翔在城樓之上夢幻般的碧青色夜空的丹頂仙鶴,以及掩映它們而升起的杏黃云霧,都是為了烘托這場大戲的核心主角——皇帝本人。
所以,如果仔細(xì)欣賞這幅被皇帝題為“瑞鶴”圖的畫作,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上面的仙鶴并非寫實(shí),而是范式化的描繪,彎著脖子飛行的仙鶴,可以從北朝隋唐以來的壁畫中,到唐宋鑄刻仙鶴飛翔紋樣的銅鏡銀器中,都找到同樣的范式形象——畫家只是對(duì)這些舊有范式巧妙地進(jìn)行排列組合,讓這群在夜空中飛翔的仙鶴看起來充滿了徘徊翱翔的動(dòng)態(tài),如果看得更加仔細(xì),你會(huì)發(fā)現(xiàn)畫面上左右飛翔的仙鶴,剛好組成了一個(gè)太極圖的樣式。

九原崗北齊墓壁畫中的仙人騎鶴與《瑞鶴圖》中的彎頸飛翔的仙鶴。

襄陽市博物館藏天馬仙鶴紋菱花鏡(局部)中的半彎頸飛鶴與《瑞鶴圖》中半彎頸飛鶴,很可能這種彎頸飛翔的仙鶴原本是用來表現(xiàn)仙人騎跨的坐騎,彎頸是為了方便仙人駕馭。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西安韓森寨唐墓出土四鶴銜綬金銀平脫鏡中的直徑飛鶴(路客看見 攝)與《瑞鶴圖》中的飛鶴。

國家博物館藏唐代高士宴樂嵌螺鈿鏡中的回首欲飛立鶴與《瑞鶴圖》中回首欲飛立鶴。

西安唐代張思九夫人胡氏墓壁畫上的立鶴與《瑞鶴圖》上鴟吻的立鶴。這種立鶴的樣式在晚唐墓葬壁畫中多見,很可能是唐代以畫鶴知名的畫家薛稷的六鶴屏風(fēng)為粉本的傳抄范式。《歷代名畫記》:“屏風(fēng)六扇鶴樣,自稷始也”。
至于那升騰的杏黃色云霧,盡管比起仙鶴,只能算是背景的背景,但它很可能同樣并非天造奇景,而是人工制造的產(chǎn)物。事實(shí)上,宋徽宗本人就是云霧制造大師,他所精心設(shè)計(jì)的假山艮岳,就是一座巨大的云霧制造機(jī),根據(jù)周密在《癸辛雜識(shí)》中的記載,艮岳“其洞中皆筑以雄黃及爐甘石,雄黃則辟蛇蝎,爐甘石則天陰能致云霧,滃鬱如深山窮谷”——不難設(shè)想為了襯托(或許也為了遮掩仙鶴的來路),人工故布迷霧,無論是對(duì)宋徽宗,還是對(duì)一心逢迎他的左右臣僚來說,并非難事。
祥瑞
無論仙鶴還是云霧的來源為何,在徽宗皇帝眼中,它們都是所謂的“祥瑞”,是自己統(tǒng)治四海升平,天命庇佑的明證。而仙鶴,對(duì)趙宋皇朝來說,還占有一個(gè)特殊地位——盡管這個(gè)特殊地位的來源頗令人尷尬——那是一個(gè)世紀(jì)前,因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而備感城下之辱的真宗皇帝,為了證明趙宋王朝的統(tǒng)治乃是天命所在,與臣下操弄起一場盛大的“天書降世”的大戲。所謂的“天書”首次降臨的地點(diǎn),正是在左承天門南角的鴟吻上。自此之后,各式各樣的祥瑞如雪片般飛向汴京,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一位名叫丁謂的寵臣所呈報(bào)的仙鶴祥瑞:
“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于殿虎之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于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dǎo)者,塞望不知其數(shù)。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dǎo)。”
丁謂奏報(bào)的仙鶴祥瑞出現(xiàn)得如此頻繁,以至于他在朝野中得了個(gè)“鶴相”的諢號(hào),某天,與他同朝為官的寇準(zhǔn)在山亭中看到了“有烏鴉數(shù)十,飛鳴而過”,于是他笑著對(duì)身邊的同僚說:“丁謂見之,當(dāng)目為玄鶴矣。”
“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后世,則后世必不信”。就像一個(gè)世紀(jì)前,一位名叫孫奭的諫官對(duì)真宗直言進(jìn)諫的那樣,這場荒誕的天書大戲,很快就隨著真宗皇帝的死亡而落幕,扈從天書下降的仙鶴,也銷聲匿跡了很長時(shí)間。一個(gè)世紀(jì)后,卻又被他的子孫徽宗皇帝重新?lián)焓捌饋怼Qb點(diǎn)在這上元節(jié)之次夕的碧青夜色中。
宋真宗像。
他想達(dá)到的目的,就像他在題詞后的詩句中所寫的那樣明確:“徘徊嘹唳當(dāng)?shù)りI,故使憧憧庶俗知”——要讓聚集在宣德門下的百姓們親眼看到這一祥瑞,讓他們相信自己的統(tǒng)治乃是天命所在,所以上天特意在上元之次夕,在皇帝正端坐在宣德樓上,俯瞰京城萬姓時(shí),降下這一仙鶴祥瑞,向大宋天下臣民,也向正在衰落的昔日強(qiáng)鄰遼國的君臣,宣示自己才是上天揀選的獨(dú)一無二的天子。
而對(duì)普通百姓來說,他們或許無法理解這群乍然出現(xiàn)在城樓上空的仙鶴背后如此之深的寓意,他們甚至很可能只是將其看作一場充滿驚喜的盛大表演。畢竟,無論是這群來而復(fù)去的仙鶴,還是描繪這群仙鶴的畫作,都與他們無關(guān)。
但從個(gè)體的角度,對(duì)閻德源來說,這群仙鶴卻有意無意之間與自己產(chǎn)生了某種聯(lián)系。就在仙鶴飛來的八天后,徽宗皇帝頒布了一則詔書“釋教修設(shè)水陸及禳道場,輒將道教神位相參者,僧尼以違制論。主首知而不舉,與同罪。著為令”——僧人將道教神位陳列在佛菩薩之間,竟然成了違反皇帝制令的大罪,僧道之間的地位,在這道詔書中高下立判。
閻德源很可能就是在這前后進(jìn)入道觀,成了一名道士。對(duì)汴京的城市貧民來說,在徽宗一朝將道士作為一項(xiàng)職業(yè),是個(gè)不錯(cuò)的選擇。
在瑞鶴飛來的五年前,徽宗皇帝就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對(duì)道門的明顯偏愛,大觀元年二月他頒布了一道御批:“道士序位令在僧上,女冠在尼上”,次年五月,他又將道門女冠的撥放名額,從原先的三十人增加到七十人。讓徽宗皇帝對(duì)道門的偏袒一發(fā)不可收的,則是他在仙鶴祥瑞的一年前所做的一個(gè)夢。那時(shí)他病了一百余天才稍稍康復(fù),就在病情好轉(zhuǎn)的第二天晚上,他夢到有人召見自己,到達(dá)那里時(shí),他發(fā)現(xiàn)是一座宮觀,左右兩旁也出現(xiàn)了兩名道士,作為儐相引導(dǎo)他走到了一座道壇上,對(duì)他說:“汝以宿命,當(dāng)興吾教”。醒來后,“始大修宮觀于禁中”。第二年正月十六出現(xiàn)在宣德門上的仙鶴祥瑞,似乎是再次印證了這個(gè)賦予徽宗皇帝振興道教使命的夢。
宋徽宗款《聽琴圖》,其中彈琴者被認(rèn)為正是徽宗本人,而坐中聽琴的兩個(gè)人,著青衣者被認(rèn)為是宋末六賊之一奸臣王黼,而著紅衣者則被認(rèn)為是奸相蔡京。
仙鶴正是道教仙禽,而道士則被稱為羽客,因此,在皇權(quán)的提拔下,道士的地位也隨著這騰空的仙鶴一飛沖天。閻德源在這一時(shí)期入道,是否存有投機(jī)的心理,不會(huì)有人知曉,唯一知道的是,他確實(shí)拜在了當(dāng)時(shí)圣眷優(yōu)渥的高道張?zhí)摪组T下。對(duì)這位經(jīng)常出入禁宮掖庭的金門羽客來說,那座將平民百姓阻擋在外的高大的宣德門,自然也無法阻擋他的腳步。
但與那些借皇帝恩寵以博取權(quán)勢的道士不同,閻德源的師父張?zhí)摪讌s是一位與眾不同的異人,他經(jīng)常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枕著皇帝的膝蓋躺下,無所避諱地說著醉話。皇帝也對(duì)他格外優(yōu)容,只是說:“張胡,汝醉也。”
直到仙鶴祥瑞的十三年后,大宋王朝再一次迎來了一場“祥瑞”——在宋金聯(lián)軍的南北夾擊下,宋朝的大敵遼國終于覆滅,遼國的末代君主天祚帝被金人俘獲。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兩場“祥瑞”之間,甚至也存在著某種草蛇灰線一般的聯(lián)系。聯(lián)絡(luò)當(dāng)時(shí)尚未建金立國的女真人夾擊遼國的計(jì)劃,正是在鶴唳城樓的祥瑞發(fā)生的這一年由圖謀走向?qū)嵭械摹?/span>
三個(gè)月前,以賀壽為名出使遼國的寵臣童貫,在返程行至盧溝河時(shí),遇到了一位名叫馬植的遼人,馬植本是遼國世家大族,仕為光祿卿,卻因“行污而內(nèi)亂,不齒于人”,因此決心冒險(xiǎn)叛投宋國,就在那個(gè)寒冷的夜晚,他向童貫描繪了一幅聯(lián)合女真夾擊遼國的宏圖愿景,就在他滔滔訴說時(shí),他或許也在童貫眼中看到了灼燒的貪欲之火。這位剛剛在青唐之戰(zhàn)中挫敗西夏的寵臣,同樣也正夢想著覆滅遼國,收復(fù)宋朝列祖列宗念茲在茲的燕云十六州的不世之功,加諸在自己頭上。于是,他倆一拍即合,馬植被童貫按插在使團(tuán)隊(duì)伍中一同回到這座仙鶴祥瑞降臨的帝都。
十三年后,來報(bào)遼國末帝被俘的金朝使節(jié),在徽宗皇帝眼中無異于又一只飛來皇城散布祥瑞的仙鶴。喜出望外的皇帝在宴請(qǐng)金朝使臣后,特意向張?zhí)摪讏?bào)喜,而張?zhí)摪茁犨^之后,只是淡淡地回答道:
“天祚在海上,筑宮室以待陛下久矣。”
徽宗皇帝并未發(fā)怒,只是沉了沉才徐徐說道:
“張胡,汝又醉也。”
可這一次,他沒醉。
鶴唳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
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xué)仙冢累累。
閻德源想必聽說過這個(gè)故事,遼東一位名叫丁令威的人,離家學(xué)道成仙,千年后,化作一只仙鶴飛回了家鄉(xiāng),站在城門的華表柱上。當(dāng)?shù)k發(fā)現(xiàn)一位家鄉(xiāng)的少年正舉著彈弓瞄準(zhǔn)自己時(shí),祂飛走了,徘徊在空中留下了這句話。
丁令威化鶴的傳奇,幾乎可以視為徽宗朝仙鶴祥瑞的前身,只是一個(gè)站在華表上,而另一個(gè)則站在鴟吻上。但丁令威化作的仙鶴留下了仙語流傳后世,而宋徽宗的仙鶴,卻只是發(fā)出了禽鳥本該有的鳴叫。但它們最終都飛走了,再也沒有回來。
神仙之所以是神仙,就在于祂們只是在天上高高俯瞰人間,只是偶爾現(xiàn)身點(diǎn)化世人;同樣,祥瑞之所以是祥瑞,也是因?yàn)樗驹撊绱讼∮校辉跉v史上難得出現(xiàn)的清平盛世才會(huì)現(xiàn)身。而并非盛世出現(xiàn)的祥瑞,就像先賢所說的那樣:
“凡瑞興非時(shí),則為妖孽”。
《瑞鶴圖》的仙鶴,究竟是祥瑞還是妖孽?天時(shí)或許真的可以作為一個(gè)判斷標(biāo)準(zhǔn)。鶴唳城樓的祥瑞發(fā)生的前一年,異常的酷寒天氣席卷大宋南北,這股寒氣甚至導(dǎo)致洞庭地區(qū)“積雪尺余,河水盡冰”,而這種酷寒天氣,早在徽宗即位前就已開始出現(xiàn),到政和元年達(dá)到高潮,“傷麥”“損桑”“人多凍死”之類的記述頻繁地出現(xiàn)在史書上。極端異常天氣的一個(gè)直接后果就是導(dǎo)致百姓生計(jì)艱難。就在祥瑞出現(xiàn)的這一年,宣州一位名叫呂堂的文士上書朝廷,描述了自己家鄉(xiāng)普遍存在的一種現(xiàn)象“薅子”:“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xí)俗相傳,謂之薅子,即其土風(fēng),宣州為甚,江寧次之,饒、信又次之”——父母為了生計(jì),竟忍心殺死自己的子女。
一面是仙鶴飛鳴的所謂祥瑞,一面是父母被迫殺死子女求活的慘劇,一種是難得一見的奇景,一種是普遍存在的現(xiàn)實(shí),如此撕裂卻又如此真切地發(fā)生在同一片土地上,那么仙鶴究竟是祥瑞,還是妖孽,答案或許已經(jīng)不言自明。而從科學(xué)理性的角度來說,仙鶴在上元次日忽然出現(xiàn)在城樓之上,很可能本身就是天時(shí)異常導(dǎo)致的結(jié)果。當(dāng)時(shí)的地球正進(jìn)入一個(gè)寒冷期,或許正是異常寒冷的氣候?qū)е孪生Q遷徙異常,因此異常地出現(xiàn)在汴京的城樓之上,成為了大宋君臣眼中的“祥瑞”。
閻德源的師父張?zhí)摪谆蛟S早已對(duì)這個(gè)答案了然于心,盡管他從未正面回答,但他在仙鶴祥瑞的十三年后對(duì)徽宗皇帝所說的那句預(yù)言,卻從另一個(gè)角度給了這個(gè)問題以答案。
就在預(yù)言的兩年后,同樣是一個(gè)時(shí)近上元的凜冬寒日,金軍攻陷了東京汴梁,俘獲了徽宗和他的兒子欽宗,將其一并押解北上,與兩年前俘獲的天祚帝殊途同歸。
他們的歸宿,正是仙鶴真正的棲息地東北——當(dāng)年飛來的仙鶴,終于把他和他的王朝一并帶走了。
兵荒馬亂中,閻德源逃走了,逃往大同,這座昔日大宋仇敵遼國的西京,如今已經(jīng)是金人的土地。這一年,他剛剛?cè)畾q。
逃亡路上,可以想見他有多少次親身與死亡擦肩而過。他的身后,是已經(jīng)在金人鐵蹄下淪為修羅地獄的中原故土。一位名叫莊綽的文士如此描述當(dāng)時(shí)的殘酷光景:“自靖康丙午歲,金人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諸路,荊榛千里,斗米至數(shù)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用。”而他所逃往的大同,在四年前剛剛遭遇金人的兵燹之劫。因?yàn)閻篮薮笸娒竦牡挚梗疖娫诠ハ荽笸筮M(jìn)行了一場殘忍的屠殺,恐怖的光景,一如靖康之變之于宋人一般,長久地烙印在大同人的記憶中,“攻城破,驅(qū)壯士無榆坡盡殺之。中有喉絲不斷者,亦枕藉積尸中”,“群兒亂走,追及者皆以大棓擊殺之”。
一路上,閻德源應(yīng)該還可以看到路旁尚未掩埋的骸骨,皮肉早已被野狗啃噬一盡,當(dāng)他到達(dá)大同,他會(huì)看到那兩座巨大的廢墟,它們?cè)臼沁|國西京最恢宏的兩座寺院大華嚴(yán)寺和大普恩寺,“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閣樓觀,俄而灰之”,“樓閣飛為埃坌,殿堂聚為瓦礫。前日棟宇所僅存者,十不三四。驕兵悍卒指為列屯,而喧寂頓殊;掠藏俘獲紛然錯(cuò)處,而垢凈俄變。殘僧去之而飲泣,遺黎過之而增欷”。
但他應(yīng)該也會(huì)看到在廢墟中往來的工匠,被兵火燒灼的殿堂,正在恢復(fù)舊日的容顏,一如昔日血肉橫飛的街市,滌凈了尸骨和血淚,再度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他決定留在這里了。
或許真的有所謂天命,更可能是他確實(shí)深諳道家衛(wèi)生之道,直到如何和光同塵。關(guān)于這兩個(gè)詞,可以有兩種理解。但確定的結(jié)果是,他一直活到了那個(gè)時(shí)代普通人難以企及的九十六歲高壽。
沒有證據(jù)顯示閻德源回過汴京,即使回去,眼中的汴京也已經(jīng)不再是舊日模樣。靖康之變的四十二年后,一位名叫樓鑰的南宋官員,奉命出使金國。當(dāng)他抵達(dá)昔日的故都汴梁——如今金人的南京時(shí),他看到接待使者的承應(yīng)人“或跪或喏,跪者北禮,喏者猶是中原禮數(shù),語音亦有微帶燕音者“——長久生活在金人的統(tǒng)治下,已經(jīng)讓他們忘卻了故國的禮儀語言,這讓他“尤使人傷嘆”。當(dāng)他路過昔日宣德門時(shí),他看到昔日恢宏壯麗的故宮,已經(jīng)因金海陵王之亂“遺火殆盡”。他也看到了令人慨嘆的一幕,“卻亭驛”原本是大宋用以接待遼國使臣的“上元驛”,如今,這兩個(gè)王朝皆已殊途同歸,只有這處屋舍依如故舊,“但西遍已廢為瓦子”。在昔日宋遼交界的真定府,樓鑰在道旁看到了三四個(gè)老婦,她們白發(fā)蒼蒼,對(duì)著自己指指點(diǎn)點(diǎn)地說道:
“此我大宋人也,我輩只見得這一次,在死也甘心。”
樓鑰能回報(bào)這些故國遺民的,只有“相與泣下”的幾許眼淚而已。
人民如故城郭非。昔日汴京,已如仙鶴飛去,但汴京的影子,猶如鶴唳的余聲,似乎又在另一座都城尋到幾分痕跡。金人的權(quán)力樞軸中都燕京的營建,“一依汴京制度”,甚至宮殿的“屏扆窗牖,亦皆由破汴都輦致于此”,金人皇家苑囿妝點(diǎn)的奇石,則是宋徽宗那可以營造祥云的艮岳山石——汴京最后的繁華,又以這種諷刺的方式,在敵國的都城中再度復(fù)活。
巖山寺金代壁畫上的宮闕,創(chuàng)建于金正隆三年,畫匠王奎在靖康之變時(shí)28歲,被認(rèn)為是當(dāng)年被金人擄走的汴京工匠之一。他在壁畫中繪制的宮闕城池市井樣貌,既像是昔日的汴京,又像是如今的燕京。
樓鑰抵達(dá)金人燕京的這一年,閻德源也正在這里,這一年,他72歲了,這位前朝小道士,顯然與新的金人統(tǒng)治者相處融洽,就像當(dāng)初徽宗皇帝圣寵優(yōu)渥的道士們一樣,他也贏得了西京的“貴戚、公侯、大夫、士庶敬之如神”。他是“西京路傳戒壇主清虛大師”,當(dāng)朝金世宗皇帝稱贊他“真在世之仙人耳”。
在樓鑰到來的數(shù)月前,他奉詔從大同前往燕京,主持重修中的燕京十方大天長觀。
當(dāng)他來到燕京時(shí),他是否能辨認(rèn)出幾許少時(shí)汴京的模樣?他是否會(huì)佇立在被稱為“宣陽門”的燕京皇城大門前,認(rèn)出幾分昔日宣德門的光景?
答案就像《瑞鶴圖》中仙鶴的來源一樣,無人知曉,唯一確定的是,他離開燕京后,并沒有回到汴京,而是重新回到了大同。
只是,當(dāng)他臨終時(shí),他卻對(duì)身邊的弟子留下了這樣一段遺言:
“云中故俗,人亡則聚薪而焚之,吾所弗欲也。當(dāng)以遺骸瘞之于丈室之后,無擾鄉(xiāng)人。”
閻德源墓志銘拓片。
我們無法揣測閻德源留下這樣的遺言個(gè)中是否有更深的含義。畢竟,比起在前朝大宋三十年的少年時(shí)光,他在新朝大金生活的歲月乃是前者的兩倍。 但死后焚化遺體,乃是所謂的“契丹遺風(fēng)”,在目前已發(fā)掘的數(shù)百座遼墓中,火葬墓占三分之一。金代遼后,這一舊俗依然延續(xù),甚至成了南宋人眼中所謂的“北俗”。但在閻德源少年時(shí)代生活的宋朝,焚化遺體卻被認(rèn)為是有傷孝道的悖逆之舉,為宋朝法令所禁止。
據(jù)說在死前的一瞬,全部的人生過往都會(huì)在腦海中快速經(jīng)過。或許,在那一瞬,他曾回到了十八歲那年,那個(gè)少年郎站在宣德門前,在推搡的人潮中擠出了一個(gè)縫隙,透過這個(gè)縫隙,他仰望著城樓上那碧青色澄澈的夜空,在升騰云霧之間,潔白的仙鶴在徘徊翱翔,發(fā)出聲聲鶴唳,震碎嘈雜的人世喧嚷,傳到了他的耳畔。
就像他臨終前身著的鶴氅,上面小小的仙鶴,伴隨著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氣。
那宋徽宗畫上的仙鶴,終于落在了他的衣袂上。
閻德源下葬時(shí)身著的鶴氅。
本文系獨(dú)家原創(chuàng)內(nèi)容。作者:李夏恩;編輯:西西;校對(duì):薛京寧 陳荻雁。歡迎轉(zhuǎn)發(fā)至朋友圈。 文末含《寫童書的人》本廣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責(zé)任編輯:
版權(quán)聲明:本篇文章由朝夕友人官網(wǎng)小編編輯,僅限于學(xué)習(xí)交流,非商業(yè)用途,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若有來源標(biāo)注錯(cuò)誤或侵權(quán),請(qǐng)?jiān)诤笈_(tái)留言聯(lián)系小編,將及時(shí)更正、刪除。
上一篇:她們穿過很多條紋衫,還有很多明星同款。又來給你們種(拔)草啦 下一篇:服飾大秀| 服飾類品牌logo設(shè)計(jì)七例
返回上一層